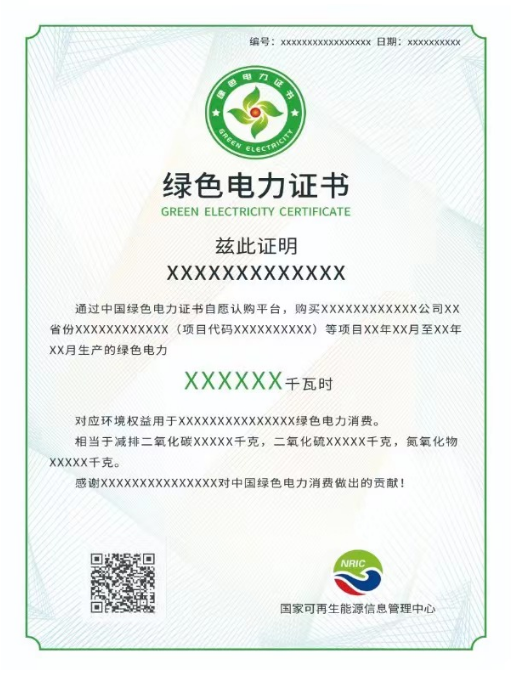
近期,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國家能源局聯合發布了《關于做好可再生能源綠色電力證書全覆蓋工作 促進可再生能源電力消費的通知》,提出研究推進綠證與全國碳排放權交易機制的銜接協調。這是我國繼提出研究在碳排放量核算中將綠色電力相關碳排放量予以扣減的可行性后,首次明確了以綠證進行市場銜接。今年3月開始,天津、北京、上海碳市場陸續允許綠色電力按零排放進行核算。不同的是,天津綠電和綠證都在抵扣范圍內、北京僅允許綠電抵扣、上海的抵扣范圍為省間綠電交易。當前,地方碳市場抵扣規則的不同有本地化需求的考量,在《通知》明確提出綠證全覆蓋以及綠證作為可再生能源電力生產消費的唯一憑證后,有待進一步完善綠證與碳市場銜接的相關機制設計。
綠證與碳市場銜接模式
這種模式,以電力用戶購買的綠證作為依據,通過綠證對應的電量折算進行碳排放量抵扣。可用于抵扣的綠證包括參與綠電交易獲得的綠證(證電合一模式)、也包括直接參與綠證交易單獨購買的綠證(證電分離模式)。
綠證與碳市場銜接的內在機理:先將綠證作為綠色電力環境外部性價值的唯一憑證,再將這部分價值通過解決碳排放外部性的經濟手段(即碳市場)予以兌現。綠證抵扣碳排放制度,一方面能夠激勵市場主體購買綠證,為綠色電力的環境外部性付費,從而為綠色電力的可持續發展提供資金支持;另一方面,這部分碳減排成本又將在碳市場中進一步傳導至其他控排主體,即真正為環境付費的是那些沒有購買綠色電力或者高排放的主體,從而實現“誰排放、誰付費”的目的。
綠證銜接的模式在業內引發過一些質疑,其中最主要的是綠證的額外性問題。部分學者研究指出,由于市場中的綠證供應量遠大于碳市場中的綠證需求,存量綠證的存在將會稀釋新增綠證的消費需求,綠證抵扣模式無法實際促進可再生能源替代高碳機組進行增量發電,不存在碳減排方面的額外性。同時,綠證已經能為新能源機組提供必要補償,也不存在經濟上的額外性。這兩點與碳抵消機制的出發點存在相悖之處。
對于上述問題,其本質在于綠證與碳市場銜接的理論基礎與CCER等碳減排信用產品的碳抵消機制是否相同。從抵扣機理看,前者是在電力間接碳排放的核算規則上進行優化,即統一的排放因子不盡合理,綠色電力的排放因子應該為零;而后者是一種補充激勵機制,抵扣范圍不區分直接排放或間接排放。因此,綠證抵扣與碳抵消機制本質存在不同,額外性不應成為綠證抵扣的必要條件。此外,若一定要考慮額外性問題,對于減排額外性,可通過限制用于抵扣的綠證范圍來實現,例如《通知》中已明確通過兩年內的綠證開展綠色電力消費認證;對于經濟額外性,綠證抵扣模式只改變了為環境付費的主體,現階段并不改變其經濟額外性。因此,推動綠證與碳市場銜接能夠有效發揮綠色電力消費與碳市場在推動能源低碳轉型中的協同作用。
未來需要關注的問題
抵扣標準的問題
目前,已允許綠色電力消費抵扣碳排放的地方碳市場中普遍采取了直接扣減電量模式,相當于按主體所在碳市場的排放因子計算減排量,在允許異地綠證抵扣的情況下,可能與綠證標識的減排量存在差異,從而引起一定的爭議,存在如何設置抵扣標準的問題。
綠證抵扣碳排放量的標準設置與政策目標導向密切相關。若僅從激勵綠電消費,提升綠證交易總量的角度出發,可按照統一的排放因子(如主體所在碳市場采用的排放因子)進行折算;若考慮綠證的區域性差異,進一步引導高排放地區的新能源發展,則可采取差異化的排放因子,向可再生能源占比較低地區的綠證抵扣進行一定傾斜。
環境權益多方主張問題
隨著未來消納權重落實到電力用戶,綠證既可以用于可再生能源電力消納責任履約,也能用于碳排放量抵扣,而這將產生是否允許已用于履約的綠證再次在碳市場中兌現權益的問題。
就上述兩個政策體系而言,是否允許綠證反映的環境權益兩次兌現主要與二者在推動電源結構轉型中的定位有關。允許兩次兌現,意味著促進可再生能源發展目標的政策工具是消納保障機制,碳市場是減排成本疏導的載體。這種情況下,綠證在兩個政策體系中的功能不同。前者代表強制性責任,后者反映減排補償,無論強制綠證或自愿綠證均可通過碳市場進行權益兌現。不允許兩次兌現,意味著消納保障機制和碳排放權交易機制均是促進可再生能源發展目標的政策工具。這種情況下,碳市場具備了可再生能源消納保障的補充機制屬性,以激勵自愿綠證消費的方式促進可再生能源發展。此時,同一綠證反映的環境權益不應再重復使用,需要通過溯源追蹤認證相關技術支撐確保同一綠色電力產品環境權益的唯一性。
可抵扣的綠證范圍問題
《通知》明確提出綠證核發范圍,包括風電、太陽能發電、常規水電、生物質發電等可再生能源發電項目。其中,存量常規水電不核發可交易綠證,2023年以后新投產的市場化常規水電可核發可交易綠證。由于市場中存在多種綠證,在推動綠證與碳市場銜接的工作中,有必要明確可以抵扣的綠證范圍。
綜上,推動綠證在碳市場中予以抵扣,本質是將相關市場主體付出的減排成本在碳市場中進行傳導。對于可交易綠證而言,無論產生綠證的電源類型是什么,市場主體均付出了額外的環境成本,因此應允許該類型綠證的成本予以傳導;對于無償核發的綠證而言,市場主體并未付出減排成本,因此也不滿足抵扣的基本條件。
相關建議
一是完善碳市場核算規則,加強綠證抵扣的相關標準制度體系建設。推動納入用電行業的碳市場完善配額分配及排放核算規則,基于“誰排放、誰付費”原則,將綠證作為綠色電力環境外部性的憑證,以綠證抵扣方式與碳市場進行銜接。加強與綠證抵扣相關的標準制度體系建設,優化碳排放因子測算方法、明確綠證抵扣范圍與抵扣方法,做好與碳排放“雙控”政策轉型的銜接。
二是推動可再生能源消納責任權重落實到電力用戶,以綠證作為唯一履約憑證并明確其使用范圍。進一步推動各地區將可再生能源消納責任權重指標落實到電力用戶等主體,以綠證作為履約的唯一憑證。統籌考慮政策工具與政策目標的匹配性、政策執行成本等要素,可酌情考慮允許同一綠證作為完成消納責任權重和抵扣碳排放量的憑證,滿足市場主體就其綠色用電的環境權益進行多方主張的相關需求,并做好綠證溯源、流通、確權等環節的技術支撐。
三是擴大新能源市場化交易規模,不斷完善綠證價格的獨立形成機制。繼續推動新能源參與電力市場交易,提高綠電綠證交易積極性,通過在綠電交易中剝離綠證價格、單獨開展綠證交易等方式,適度結合碳市場建設情況,不斷完善綠證價格形成機制,逐步建立起獨立的綠證定價機制。條件成熟時,允許綠證多次交易。
特別聲明:本網站轉載的所有內容,均已署名來源與作者,版權歸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權,請聯系我們刪除。凡來源注明低碳網的內容為低碳網原創,轉載需注明來源。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